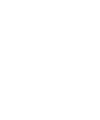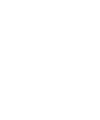龙族:她们和路明非一起归来 - 第10章 梦(一)
卯时的雾气还在青石板路上流淌,路明非推开铁匠铺的榆木门,扫去露水点燃了熔炉。
墙边的角落里堆放著七把还未成型的镰刀铁胚子。
他双手哈著热气,在灶台底部点火,確认火势足够稳定之后,起身站在风箱旁。
在拉动风箱的瞬间,火星如金蛇窜上房梁,他习惯性侧身挡住熟睡的阿棠。
少女在草蓆上翻了个身,似乎杂音对她的睡眠没有任何影响,反而舔了舔嘴角,把用他磨破的旧衣缝的,露出半截线头的粗布娃娃抱得更紧了。
趁著铁胚子还在预热,路明非解开缠手的麻布,掌心交错的新旧伤疤在晨雾中泛白。
取下掛在樑上的粗布包袱,里面裹著昨夜从东家厨房摸来的两个杂麵饃。
仔细剥去烤焦的外皮,把完好的部分掰成小块泡进热水,自己却嚼著那些炭黑的碎屑。
“鐺!”
第一锤砸在烧红的铁料上,路明非的虎口在晨风中裂开细纹。
阿棠揉著还未完全的眼睛坐起来,双手鬆开布娃娃在床上乱摸像是在寻找什么,嘴里小声喊著:“哥,你在哪儿?”
直到路明非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,才安下心来。
她一手抱著满是哥哥气息的粗布娃娃,一手端起草蓆上的木碗,小口抿著泡软的杂麵饃,眼睛隨著哥哥打铁的动作来回摇晃。
比起藏在树洞过夜的日子,此刻硌人的硬木床和草蓆更像是天堂。
辰时的阳光刺破窗纸,铁匠铺蒸腾的煤烟裹著金属腥气钻进每条砖缝,路明非的麻布腰带被汗水浸成深褐色。
阿棠正踮脚擦拭掛在墙上的铁牌。
那是天垂镇户籍凭证,边角还留著三个月前典当命器换来的火漆印。
每当有庄稼汉想要来打造农用铁器,她都会上前招待。
少女会笑盈盈捧来粗陶碗为对方端上热水,在热气氤氳间,轻抖手腕,顺著袖口滑落三片柳叶。
接著会记下汉子想要打造的铁器,收下铜钱,计算好要用到的生铁锭。
午时的日头最毒,九尺见方的铁匠铺像个火炉,连空气都在铁锤与金属的撞击中扭曲。
正午的暴晒下铁砧烫如烙铁,路明非赤著上身锻打镰刀,铁砧在火星四溅中嗡鸣震颤,汗珠滚过占据整个后背的鞭痕,在烧红的铁块上蒸腾成白烟。
阿棠则是哼著不知名的江南小调,蹲在煤堆旁分拣石炭,这个曲调是他们逃亡途中某个船娘教的。
路明非的锤音不自觉跟著节拍,铁砧上渐渐显出镰刀的轮廓。
“噹啷!”
烧红的镰刀淬进冷水,腾起模糊的白雾,路明非在蒸汽中咳嗽,血丝顺著指缝渗进铁砧凹槽——那里积著几个月下来的锈斑与汗硷,早分不清是金属还是含著碎肉的血块。
打造镰刀的过程不繁琐,但是费时费力。
当只剩最后一个铁胚子时,窗外的太阳已经快要坠落。
“鐺——”
最后一锤落下,斜阳把风箱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隨著最后一把镰刀铸造完成,梳著双马尾的阿棠踮著脚从门帘后钻进来,怀里抱著比她脑袋还大的粗陶瓮。
“哥,喝点水。”
她把瓮放在垫著稻草的竹筐上,袖口用草绳扎得紧紧的。
现在阿棠身上穿的衣服是三个月前逃离矿坑时,他用囚衣布条给改的。
破布条原本浸著血,在溪水里搓了十七八遍才褪成现在的灰白色。
路明非抹了把脸,盐渍在睫毛上凝成白霜。
“王掌柜说这批锄头要多加三斤铁。”小姑娘蹲在风箱旁,铁钳比她胳膊还粗,“我往炉子里多添了两铲煤渣,但...但帐房先生扣了二十文钱。”
食指和中指紧紧夹住伸进两指之间的大拇指,声音怯生生的。
她很害怕哥哥会不要她,如果没有自己这个拖油瓶,哥哥一个人会活得很好。
二十文,足够两个人活很久。
可是自己只有哥哥一个亲人,如果哥哥真的不要自己,她又能去哪儿呢。
炉火映得阿棠鼻尖发亮,两只眼睛湿漉漉的。
但是路明非怎么可能会丟下她呢,正如她所想的,路明非在这个世界上,也只剩下她一个亲人了。
“阿棠,过来。”
路明非突然开口,声音比淬火的铁还嘶哑。
她磨蹭著挪到铁砧前,路明非从炉灰里扒拉出个油纸包。
焦黑的纸皮下,麦芽的甜香混著草灰瀰漫开来。
“生日要吃。”
他摸了摸女孩的头髮,然后別过头去修理崩口的铁锤。
身后传来压抑的抽泣,接著是窸窸窣窣的撕纸声。
只是哪有什么生日,他们连真实姓名都埋葬在矿场的血污里。
三个月前的那个雨夜,背著高烧昏迷的女孩蹚过冰河时,他还记得脖子旁突然传出微弱的呢喃:“阿娘说...生辰要吃...”
炉火噼啪作响。
路明非数著风箱的喘息声,身后传来带著鼻音的嘀咕:“哥,你也吃。”
阿棠举著半块凑过来,稀拉出晶莹的丝,晃悠悠映著跳动的炉火。
他摇摇头,女孩却突然把按在他开裂的虎口上,温热的浆渗入伤口,安抚著满是血污的伤口。
暮色漫进铺子时,铁砧上摆著七把镰刀。
阿棠已经热好杂粮饼,两人坐在缺了一角的木桌上就著野菜汤吃饭。
“今天绣庄刘婶教了我锁边针。”
吃饭时阿棠突然开口,杂粮饼的碎渣掉进菜汤里。
她从针线筐底翻出块靛蓝粗布,上面歪歪扭扭地绣著两只鸭子,“是...是戏水的鸳鸯。”
路明非盯著那块布,汤勺在碗底刮出刺耳的声响。
“明天开始別去绣庄了。”他放下碗,铁匠铺的空气突然变得粘稠。
阿棠的筷子悬在半空,汤麵上浮著的油星渐渐聚成惨白的小月亮,风卷著铁屑在门外打转。
“再等个几天,哥送你去镇西女塾。”
“哥哥最坏了,就知道嚇我!”
阿棠放下筷子轻轻捶在路明非的肩膀上,脸上洋溢著笑容。
路明非则是用筷子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她的脑袋。
“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乱添煤渣。”
吃完饭,一切收拾妥当后,精疲力尽的阿棠在临睡前会去铁匠铺后墙,那一片墙上满是裂缝。
她踩著木凳把新的瓦片推进去,这是他们计算天数的工具。
现在裂缝里已经塞了九十三片。
二更天的梆子响过三遍,路明非还在修整镰刀。
九个时辰连轴转的日子,並没有让路明非感觉厌烦,比起矿场里被奴役等死,这样的生活更让他安心。
月光漏进茅草屋顶的缝隙,照在並排躺著的两个铺盖上。
阿棠蜷成小小一团,怀里依然抱著粗布娃娃。
他摸到墙缝里藏的铜钱,三百四十七枚带著体温的圆月,再多接几个单子就能送阿棠去镇西女塾。
少女打著鼾响在梦中囈语,下意识地抱住路明非,像是梦到了什么害怕的事情,流出眼泪。
路明非一边轻拍她的后背,一边唱起曾经她最喜欢的歌谣。
“阿棠,我们一定会活下去的。”
铁砧突然发出细微的震颤。
路明非拍背的手僵在半空。
又是幻觉吗?
这种震动他再熟悉不过——是马蹄铁叩击青石板的声音。
可这里是边境,矿场的人根本不可能突破封锁到这个地方。
月光將窗欞的影子拉得老长,是三个骑兵的轮廓。
“叮——”
淬火的镰刀被路明非弹指敲响,在月光下泛起幽蓝。
他轻轻掀开地砖,露出埋在灰烬下的长剑。
刀柄上缠著一圈圈染血的布条和浸过药汁的麻绳。
只有握著刀柄才能让他感受到安全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